蓝山
交还钥匙之后,穆远兀自步下经阁,在阁楼外的荷池边洗净了双手。他将手上的余水轻轻甩落,看见水珠落在舒展的荷叶上,顺着叶纹滑到叶心,晶莹剔透,仿佛是凝结的夜露。
他退出了余府,返回城中,却并没有归家,而是径直去了顾氏医馆。
他与余家还有最后一个约定没有完成。
医馆大门的钥匙他原本就有,而地窖的钥匙,昨日离开之前,郗生也给了他一份。他一扇一扇地推开医馆的馆门、堂门,一扇一扇地穿过,回身将背后的门扉一一栓实,在后堂里点上烛火,卸开暗门上的锁链,顺着旋梯往地下深处走去。地窖之中气息湿寒,光线幽暗,盖由这本是医馆置物的场所,空气中还弥漫着淡淡的药酒香气。人死之后长居地下,厚土永夜,虫蚁啮棺,个中冷寂,想来不会逊色于此。不过倘若居者是他的哥哥,应当不会为这种事而困扰吧。
窖洞之中,深广的木箱静静伫立在他的眼前。穆远掀开箱盖,小心抬起棺木上的盖板。实木沉厚,今日郗生不在,凭他一人不便搬动,他便将盖板架在木箱的沿口上,慢慢推顶出去,像是坡梯一样斜支在木箱的侧边。一日不见,棺中人的容颜仍旧那样完整而生动,棺边堆砌的冰块却已融化近半,一颗一颗浮在水面上,仿佛渐渐消逝的遗迹,将自己的生命全都渡给了棺中之人。
只是此刻,这样生动的面容,竟让他不由得憎恨起来。
穆远挽起自己的长袖,在冰水中仔仔细细地又搓洗了一遍手指,几乎将一双手都浸得麻木无觉。冰冷的指节往腰间探进穆岑的衣摆,解开裤腰的系带,勾住裤缘,从那人的腰间将素麻白布小心褪下。裸露的长腿一如既往清直如玉,长净的性器静静躺在腿根之间。
但不是的,不是那处。
他轻轻握住穆岑的脚踝,取下方才褪落的裤料,将那人的双腿曲架起来,一双膝盖尽量高抬、分开;担心这个姿势不够牢靠,又轻轻扶住了那人的膝侧。他将自己的右手伸入棺木之中,手背几乎擦着棺底,探出两根长指,慢慢地游至那人身下隐蔽的穴口,触上口缘处细密褶皱的肌肤。
他记得,当初有一次他替哥哥清理伤势,曾从后庭中取出一只丝网兜住的玉珠。而那时送那人回来的,倘若他不曾记错,应当也是余家的人。
于是他深吸一口气,阖上双眼,咬死牙关,指尖向前,手下用力,从皮肉间窄紧的洞隙中,将自己的双指一寸一寸推入了那人冰冷的后庭。
鱼形的玉石从那人身下露出翘尾时,穆远觉得,自己的心魂几乎已从身体之中飞散而去了。
他弯动指节,继续将玉石自那人的身体中全然勾出,摸索着捡拾起来,后退一步,颓然跌坐在地上。烁动的烛火中,他看见穆岑的双膝高出箱沿,在他眼前静默地伫立着,像是两座惨白的、覆雪的小山。他怔怔地仰着脖颈,目光勾住映光的山脊,有那么一刻似乎感到自己全身的骨头都被抽走了,也不知究竟在地上痴坐了多久,才终于开始一点点拼凑起自己的神智,伸手攀住木箱的侧沿,重新支撑起颤软的双腿。他的身体不稳,脚步错晃,一时间不知踏到了什么硬物,低下脑袋呆视半晌,才忽然了悟,原来是一只肥美的玉雕鱼尾——方才他跌倒之时,手中还握着那只刚刚从哥哥身体中取出的鱼符,玉石脆硬,骤然拍摔在地上,无声无息地断成了两截。
穆远沉默地收拾起地上的残块,搁在一边,转身折回棺木边,替那人仔细抚平穴口、复归身体和衣衫,又在阖好的棺木周围添置了一些新凿的碎冰。借着烛光,他用舀出的冰水将鱼符前后洗净,擎着灯台,一级一级步上了地窖的旋梯。清晨时分,他启程回到小院,从掌中递出断成两半的镶金玉石,交给了等在门口的余家管事。朝阳的暖意落在他的身上,手上,鱼符上,玉石鲤鱼雕琢细腻,栩栩如生,层层叠叠的鳞片浮泛着莹润的光泽,他才发现鳞隙之间犹然结卡着些许未能洗净的、穆岑的血迹,暗红断续,像是朱砂剥落的精巧勾边。
余家的人十分慷慨地遵守了当初的约定,从那以后再也没有来找过他。而那位被推来作祭的余少公子是活是死,他也再无心系管。穆远回到房间,将自己埋在衾枕中一连昏睡了两日,门扉不锁,万事不问,若是胃腹被饿得太疼,便胡乱从床头摸些剩余的糕饼充饥。直到第三日午后,天气暴热,院墙外的蝉鸣实在太吵,弄得他头痛欲裂,他才终于挣扎着从床榻上爬起身来,将自己打点清净,更衣上集,去往殡葬铺子,与掌柜的约定了葬祭的事宜。
下葬的前一日,穆远到医馆交还了地窖的钥匙,跟着郗生下到窖洞深处,最后看望了一次那人。他站在敞开的棺木前,向着幽深的棺木行礼作别,上前一步,为那人沉静的面容覆上了一张洁白的丝绢。棺盖落下之时,同行的郗生从身侧为他递来了长钉和槌头,他遂绕着棺木,亲手下钉,将整具灵柩一槌一槌地钉死。木箱中的冰块融化殆尽,余水被郗生用竹管引出。于是他便知道,从今往后,灵柩里的人也终于将同那些他曾经或爱或憎或是全不相识的人一样,此生此世、天涯碧落,都再不会相见了。
六月十一,送葬的队伍从凌秋门外缓缓驶出。盛夏的太阳在今日少有地慈爱起来,躲藏在暄厚的白云背后,让清蝉和惠风占了先机。水田之中夏稻正满,翠浪摇曳,畦垄边有小憩的白鹭,临水梳整着莹洁漂亮的白羽。
天际尽头伫立着葱郁而灰蓝的孤南山。
少小时第一次被哥哥带着上山游玩、识草寻木,穆远才发现,原来灰蓝色的孤南山其实并不真是蓝色的——理所当然,山怎么会是蓝色的。只是在那之后,他时不时便要想起《逍遥游》里那句漫无边际的话:“天之苍苍,其正色邪?其远而无所至极邪?”
他看不清孤南山的颜色,正如他看不清天空的颜色和穆岑的颜色。他才终于慢慢明白,世间极远的不仅是苍山和天幕,也可以是同一片屋瓦下飘摇与共的人。
他将穆岑葬在了孤南山山腰视野开阔之处,树荫掩映,隔着一道山溪,与父母的衣冠冢遥遥相望——他们的父母死于江海之上,波涛浩瀚,并无尸身可寻。穆远记得,当年衣冠落葬时,他的哥哥尚且有伤在身,勉强随送葬队伍行至山脚之下,已然体力难支,故而并未真正上到此处,合坟之式则委托管家胡伯代为主持。那时他也自请离开了队伍,往附近的亭阁中陪着哥哥稍作歇息,坐在那人的身边,握住那人与当时天气极不相称的、冰冷的手。只是没想到,转眼之间,他便再次踏上这条道路,将那人也送入了幽冥。出殡之时,他照习俗随着那人的棺柩一路抛洒了漫天的纸钱。镂空的圆片纷扬如雪,他忽然想,如果这些是诗稿,穆岑大约会更加喜欢。
秀丽的山林之间从此又多了一座新碑。葬事结束,穆远收拾起随行的残物,回望了一眼青石碑上的名刻,便同葬仪队伍一道下山,学着哥哥当年操持时的样子,为佣夫结清雇钱。归家之后,他褪去哀服,在小院的石桌边怔坐了许久,一时茫然,遂又起身信步,从城北绕到城南,绕过老屋,绕进集市,最终却止步在了酒铺之前。他的哥哥固然从不饮酒,不过少小时他倒是曾见老管家胡伯举着小杯,在案前咂摸得如痴如醉,一时好奇,便缠着胡伯也给他尝上一口,可惜未能如愿。他在酒铺中挑选片刻,最终沽回了两坛夏日才上的青梅新酿。家中没有酒杯,他便将酒液倾倒在茶杯之中。
酒气甘甜微醺,他很开怀。
那一日穆远在小院中对着孤南山自斟自酌,从傍晚一直饮至夜半,竟至睡倒在石桌之傍,翌日被洒在脸上的朝阳叫醒,头昏脑胀,却仍觉不能尽兴。于是起居过后,他遂又拎着坛子,到酒铺中改沽了两坛更为浓烈的白酒。这次他没有回家,而是往北穿过凌秋门,向外走出两个时辰,再一次拜访了孤南山上哥哥的坟墓。
孤南山分贯两州、地势佳绝。山上风光高远,草木秀郁,晴时可以远眺域外奔流的大江。借以佐酒,是再适合不过的佳景。穆远倚坐在昨日新立的石碑之前,就着树荫外渺远的天水,闲眺送饮。白酒非梅酒所比,气劲呛人,他尚耐不惯个中滋味,第一口不小心闷多了,便掩着袖子咳嗽起来,咳得一双眼睛都红红地泛起了泪花。吃过教训,他只好浅斟慢酌,从杯中一小口一小口地啜饮,每啜两口便要歇上一歇,让自己从辛辣和眩晕中缓过劲来。然而酒劲堆叠,半坛下去他还是困酒,便将就倚在石碑上浅眠片刻,转醒过后再继续斟酌。头顶林鸟相呼,分携来去,两坛酒他喝喝停停,喝到日暮时分也还没喝完。穆远望了望山侧的夕阳,又低下头,眯起一双红眼,望进酒坛里幽深摇荡的水面,不知为何觉得兴味索然,便将余酒尽数倾入坟边的溪瀑,下山归家去了。
此后的十来日,他望着孤南山朝时来,暮时去,每日都会携来气性不同的酒,靠山坐饮。酒虽同为酒,然而有的好喝,有的难喝,与人相似,幸而他都不甚介意。今年的夏日渐近尾声,这几乎成了他消磨最后一段葱郁时光的惯例。朝廷的任命书送到了他的家中,他也没什么心思过问。
六月廿四的午前,穆远起居完毕,仍如往常一样信手挽结起懒散的长发,提上酒坛,便准备出门沽酒。然而就在他动作之时,其中一只坛子的系绳却不意绷断开来,脱手扫倒在地上,摔了个稀碎。穆远怔愣片刻,到厨房取来簸箕,俯身收捡起地上的碎瓦,一片一片地投入箕斗、拿宣纸包裹起来,却忽然觉得自己仿佛是忘记了什么事。他站起身,对着手上的纸包盯了半晌,逐事回溯,才蓦地记起,先前哥哥被官差和余家下手弄乱的房间,他还未替那人收拾妥帖。
空置的酒坛终于又被他轻轻放回了案前。这一日,穆远难得没有再度光临酒铺,而是换上久违的粗麻布衫,裹上头巾,推开了家中那扇沉寂已久的房门。如今长夏将尽,中夜初凉,白昼的艳阳却仍旧势头未歇,很快便将整片大地烘烤得燥热起来。所幸穆岑的房间门扉久掩,不受风日,又经昨夜沉凉,觉起来要比户外阴爽得多。转动的门板惊扰起空中的浮尘,在透窗而入的幽光里回旋飞舞。小屋中纸墨的气息一如往常,其间还夹杂着一缕淡淡的腥膻:床榻与地板上余留的血渍虽然早已干涸,散发的余味却在所难免。整套衾褥他势必要丢弃重置,若是血渗得太深,恐怕连床板也得一并更换。
房间内仍是他当初归乡时第一眼所见的那副散乱模样,一点变化都没有——也对,房间总不会自己将自己收拾干净。穆远在门槛前低下身去,捡拾起脚边散落的残稿,轻轻拂去表面沉积的灰尘,理平纸页,抱入怀中。从前他偶尔光顾瓦舍,下场后被哥哥带着一道归家,便会像这样替那人抱着当天携带的稿本。他记得,那人写完书稿后,总是将稿纸分册,在纸缘打孔结线,再以浆糊裱边固定。不过现在,莫说还未及装订的散稿,许多原本清整的册本也已经坼裂、散乱开了。
他一沓一沓收捡着,在白花花的稿纸中清理出一条小小的通路,如是往复,才得以渐渐往房间深处移去。稿本的污损远比封面的积尘要更为棘手,不过那些,或可待稍后再逐一处置。拾汇的稿本在穆远的怀中渐渐攒成一座小山,他遂将纸山移置一旁,再攒一座;待地上的稿纸全都清捡完毕,又起身走到立柜之前,收拾起脚边绵延的藏书和杂物。搜房时不知是官差还是余家举动轻率,曾被哥哥收藏严整的瓷玉如今纷纷倒落、残损各异。穆远在其中一一分拣,倘若尚能修复,便先留置一边;实在摔得太碎的,只好记下形制花样,看日后有无机会重新购得。物堆深处,那人的曲颈琵琶也被淹埋其中,盖板和背板被生生分拆开,想来是余家人为了确认箱内有无所藏而干出的好事。修理这样精细的乐器非他所长,他还得将琵琶送到琴行去,问问琴师能不能修好。
收整完毕,穆远打开窗户,将床榻上的衾被尽数抛到院落之中,准备待明日再上集请人前来收采。地上凝结的血迹留待最后再好好刷洗,他终于得以坐到环积如山的谱卷之间小憩片刻,取来那些墨迹蜿蜒的残卷,逐张逐页专心照管。
宣纸畏水,单薄易损,又曾受慢待,清理起来也需十分小心:沾了尘秽的地方以布帕轻轻拭净,褶皱破污的用手指仔细抹展,撕裂之处则在纸背上沿着裂缝用浆糊和纸条简单修补。安置妥当,穆远便将纸本上的内容阅读一遍,从册本中找到与之前后贯通的部分,修合叠垛,拿玉石镇纸轻轻压实。这样大量的文本一次积摊开来,想要复原并非易事,又何况他一面收,一面看,仿佛要将这些年他所缺席的哥哥的书场通通补齐一般。成百个故事在他面前交织横生,宛如那人窗外风竹丛生掩映的枝叶,摇荡有声。穆岑的笔迹匀捷而秀婉,不似近年来天下流行的那样锋芒毕露、硬瘦如骨,反倒有一种春花悬丝、游龙轻矫之态。草稿中的字句亦不乏点窜涂抹,他几乎能够想见那人在案前或是榻上勾转手腕的样子。可惜字稿虽在,那人的琴曲和唱腔他再也无处寻问,偶尔碰见自己听过的稿本,想起当时台上的风光,便像是面见了亲切的故人。琵琶曲谱的记号他看不太懂,只好去繁从简,在身侧轻轻打着节拍、吟哦出曲子的主调,将偶尔断散的曲脉重新织结起来。
穆岑说了七年的书,留下的稿本让他一气收了整整一日,才堪堪收去了十之二三。自从科考结束归乡,他镇日混沌,一直没有心力读书,此番借着整理那人的书稿,忽忽沉浸其中,才渐觉心神宁定,万虑皆忘。若非坐久了肩颈僵疼,或是整个人饿到头昏眼花,他几乎要忘记时间的流逝。
或许于他而言,这些书稿比酒水还要更管用一些。
当晚穆远点着灯烛,一直收拾到夜深,实在困不过了,才熄灯回房,稍作歇息。第二日清晨,他上街买置了些糕点,便回到此处,继续起他的工作。然而正当他从纸堆里新抽了一册稿本、准备检视页面的破污,一张精巧的画稿却从页隙之间倏然飘脱,静静躺落在他的面前。他从不知那人还有作画的本领,一时愕然,拾起细看,竟是一簇迎春盛放、秾艳披拂的海棠花枝。枝条无根无干,仿佛从高墙上逾越出来一般,自稿纸的右上方斜刺而下,至末端又微微昂起。细枝之上幽花团团,刻画精细,花瓣随兴以淡色的朱砂涂抹点染,被细长的花茎悬缀着,似若美人含羞,低垂在枝条的左右。
垂丝海棠。
画面上没有署名,也没有题词,只在左上角的空白之处悬吊了一个小字:“雨。”
什么时候的雨?
穆远将画稿在眼前翻来覆去,也没再找到其它的文字,倒是那枝斜刺的花枝,姿仪幽静,低回柔艳,总叫他生出些莫名的熟稔。
或许是沧浪亭中的春景吧,他想。
他将画稿搁在一边,低下头,继续整理怀中的册本,可没想还未整理上几册,又从册本中翻出一张画稿来。画上花枝斜出,花团锦簇,与先前那张如出一辙,只不过相较起来,着花的细枝似乎要更繁茂一些。左上角的空白处仍然只记着不知何日的天气:“雨。”他遂将这张画稿也与先前找到的叠在了一处。
之后他一如惯例,仍旧从纸丘上取来稿本,将每本残册仔细翻检,直到睡前,却再也没碰见过那样的画稿;翌日继续,才见它们又露了面。那一天他总共收出了六张,虽不算多,较之昨日孤零零的两纸,却已叫人印象深刻。画中海棠的笔触时精时率,花枝或疏或密,朱色有浓有淡,相同之处,却总是独一道从右上角斜刺下去,延至枝稍却又微微翘起,似乎是同一枝花的不同光景。作画人秉承着一贯的气性,惜字如金,只肯在角落里放一个“雨”字,有时干脆一片空白,空凭一枝芳意刺破纸张。好不容易有一张记录了日期,却也显得十分怪异:“三月廿七。”
这样的日期,不应当是垂丝海棠能够开到的时节——宣州城地处江南,春日花开向来很早,垂丝海棠甚至入不了三月。
或许是春尽时的怀忆之作吧,穆远又想。
一个念头在他的脑海中隐约浮沉,仿佛海平线上遥远的鲸背,却一次又一次被他轻轻按下。直到第四日时,他的身旁还剩下最后一座纸丘,他信手从纸丘上取来一册稿本,却不小心牵带到了另外一册的扉页。他的手中一重,下意识抬起手臂,往高处一扬,于是整整一叠海棠画稿便从倾倒的稿本中散坠而出,如同跳珠流瀑,骤然泼洒在他的面前。
成片的画稿,成片的雨,成片花开正盛、秾艳含情的海棠花枝。他的身前纷纷然绽开一片花海,夏末时节的雨意和恼人的春色几乎要将他淹没。他伸出手,将面前的画稿一一拾起,玲珑的颜色从他眼前流淌而过,连带着稿纸上逐渐增多的日期:“五月初五;闰六月十八;九月廿三;七月二十。”他实在无法说服自己,若无因缘,一个人怎样才会在这样多个毫无关联的日子、这样频繁地想起同样一枝垂丝海棠,并将它们一一画下,存成如此丰厚的一叠画稿。
重叠的花海之中,他终于见到了唯一一张署“晴”的画作,画角上有幸也标注了节候,“花朝”,二月十二,或许真的夹杂了些许那人对沧浪亭中海棠花树的实写:花枝梢头栖息着一只敛翅的蝴蝶,仿佛刚刚停落下来,动作轻悄,却还是颤落了一片柔艳的花瓣。
穆远静默地闭上了眼睛。
其实他何尝不知,这样一枝穷极姿韵、四时绝艳的海棠花,他并不是没有见过——不如说,他根本从来没有忘记。那是在红尘纷扬的京城之中,春深将暮的时节。只不过,那株海棠并非有如它的同类一般生自土中,而是盛开在一个人的身前。
一个拥有琥珀色剪水双瞳,曾经夜半鼓琴、与他言笑相向的人。
他记得那人言及江南,道:“只是有故人在彼处罢了。”
所以到头来,连你也是他的“客人”吗?
穆远探出指尖,轻轻抚上那只蝴蝶的广翅,像是抚上什么人身前的肌肤,想起那人眼底总是清浅的笑意,忽然间谑笑了一声:命运到底要作弄他到什么时候?
他沉默着收攥起自己的手指,低下头,继续处置完剩下的书稿与曲谱,将所有收出的海棠画稿叠合到书案上,压好镇纸,回了房间。翌日清晨,他抱着穆岑损坏的琵琶去了琴行,路过酒铺,又开始沽酒访山,沉醉起来。七月初的一个黄昏,他下到山脚,正欲归家,却不意碰上了一场带阳的大雨。他站在附近的亭阁中等了一会儿,不见雨势转小,便脱下鞋袜,拎在手上,信步走进了雨幕之中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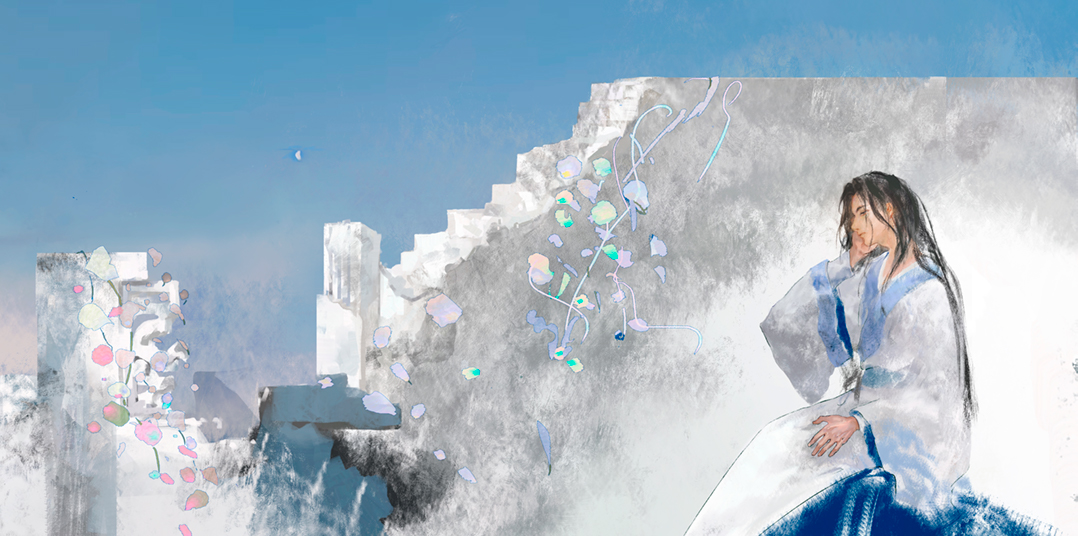
Image by OBQ. All rights reserved.